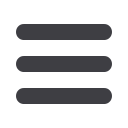

528
歐美研究
義務等),茲事體大。若欲要求取證地執法者知曉、注意並遵守審判地
法,那麼,本來就「環環相扣」的司法互助,從「前端」開始,就要
先考慮「如何」(以立法層面及外交途徑來)
達成這個困難任務的先決
問題。否則,如果完全欠缺內國立法規範及司法互助協議的基礎,只
顧在「後端」的個案採取「證據取得及使用皆依審判地法說」的結果,
不但不切實際
(亦即,實際上取證地執法者並未依審判地法),並將進
而造成外國合法取證被審判地法院大量摒棄不用的後果。一言以蔽
之,審判地說本身仍「不足以自行」,必須從「前端」的基礎開始,就
輔以其他的指導原則和配套作法,始能完足
(下文伍)。
至於區分說,除了也有「前端、後端」如何配合的相同問題外,
還有其自身的困境。例如前述例
2
所示,即便依照區分說,還是同樣
可能產生次等被告問題,因為未予質問保障的取證過程,依照取證地
法剛好就是完全合法的情形,此時,區分說要如何處理呢?更何況如
果不能從證據取得違法就直接導出禁止使用,而禁止使用也不以違法
取證為限,那麼,到底重心放在取證地合法與否的意義何在呢?
參、我國最高法院的內國傳聞取徑
一、實務取向:以內國傳聞法則為圭臬
前述司法互助案件的漏洞和困境,究竟解決的出路何在?在引介
歐洲人權法院的標竿裁判之前,先看一下我國最高法院的處置方式。
應予說明,儘管司法互助或境外取證之刑事案件,隨著國際交流頻繁
而與日俱增,但遺憾的是,我國實務對於國際司法互助的認知和視野,
卻是頗為狹隘,甚而出現嚴重違反國際慣例之處置。
15
再者,司法互
15
例如
98
年度台上字第
1941
號判決,檢察官私下在境外行使我國司法主權,而法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