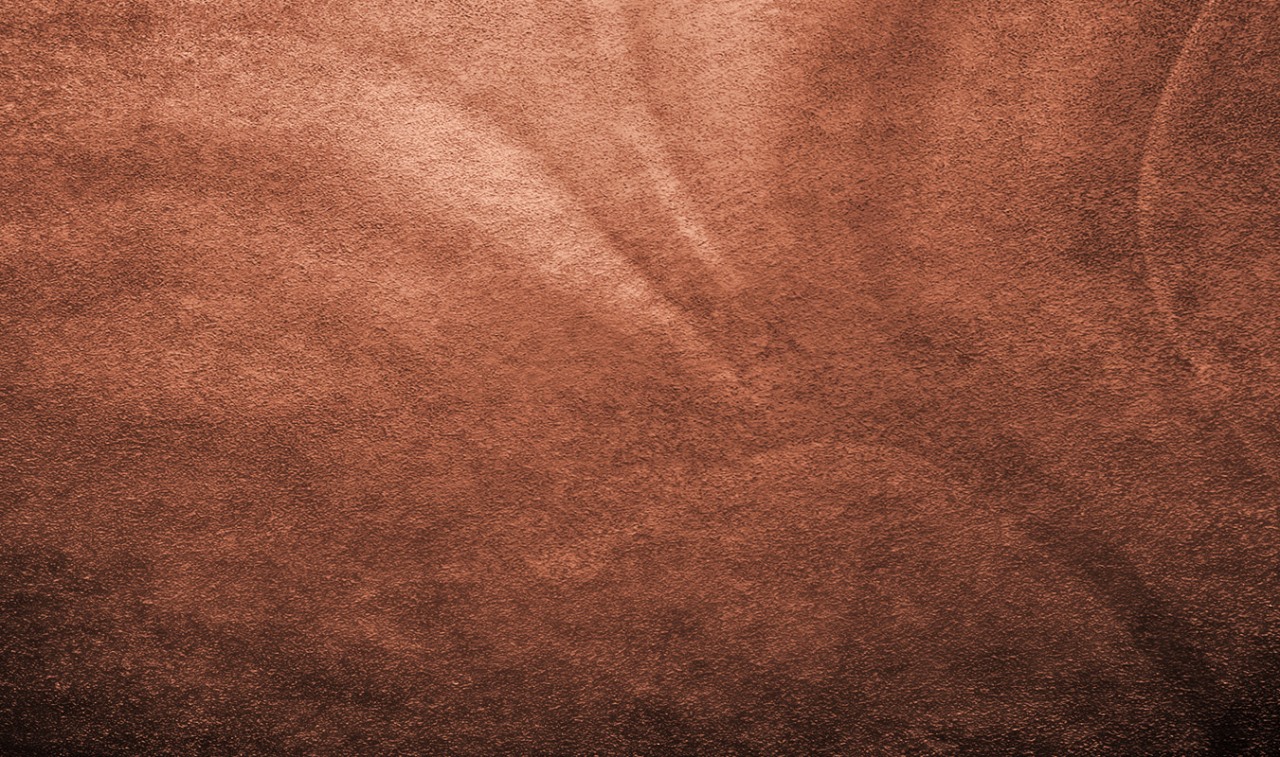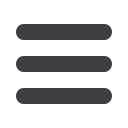

抒情敘事詩與濟慈之詩人本體的認同
263
白色的山楂和野薔薇
蓋在葉子下迅速凋萎的紫羅蘭;
五月中旬最大的小孩,
正在綻放的麝香玫瑰,上面的露珠有如酒般。
(
第
46-49
行
)
這個詩節除了在客觀的敘說中揉合了主觀的情思外,亦提供了一個
解讀時空的重要向度。詩人先描述其周遭的環境,再提及他對季節
的直覺感受;一個敘事即因此而展開。史柏利以為這個詩節是一個
成功的共感覺 (
synesthesia
) 的意象 (
Sperry, 1973
:
265
)。但是,或
許可有另個解釋:表面上,濟慈成功地建造了一個莎士比亞般的花
園 (
Allott
,
1970
:
528
)。
23
然而,在深層的含義中,他的幻想第二
次破滅,而現實感再度入侵。在描繪愉悅的夏夜時,此詩行「夏日
傍晚蒼蠅的纏飛」(第
50
行),在未來濟慈的醒悟中,變成了第二個
象徵性的線索。對此,范德勒以為蒼蠅的嗡嗡聲表示了詩人正處於
其「天堂般的幻想」之最後階段 (
Vendler, 1983
:
92
)。但如上述,
此詩行或許隱喻了醜陋的現實,而這是濟慈的個人感知。蒼蠅的嗡
嗡聲破壞了美麗的景象,營造出與前文大相徑庭的強烈對比,而形
成了一個相反敘事。由此可知,嗡嗡的蒼蠅聲之意涵很深,因其象
徵了夜鶯的世界並非完美。此外,該字眼「纏」(
haunt
) 也加強了
令人厭惡的感覺。這些外相交雜了個人的感受,為將來詩人必得改
變立場而心情惆悵預留了伏筆。但是,到目前為止,詩人並未留心
此線索;他仍一樣地情執於鳥兒的世界。
全詩中,第六個詩節是最可看出詩人主觀的情思。詩人對夜鶯
世界的認同於此時達到了高峰;於是,其內心深處的想法即逐漸浮
上檯面。在描述外境時,鳥兒的世界喚起了詩人的死亡欲望 (
death
23
濟慈或許受到莎士比亞《仲夏夜之夢》
(
A Midsummer Night’s Dream
II, i, 249-52
)
的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