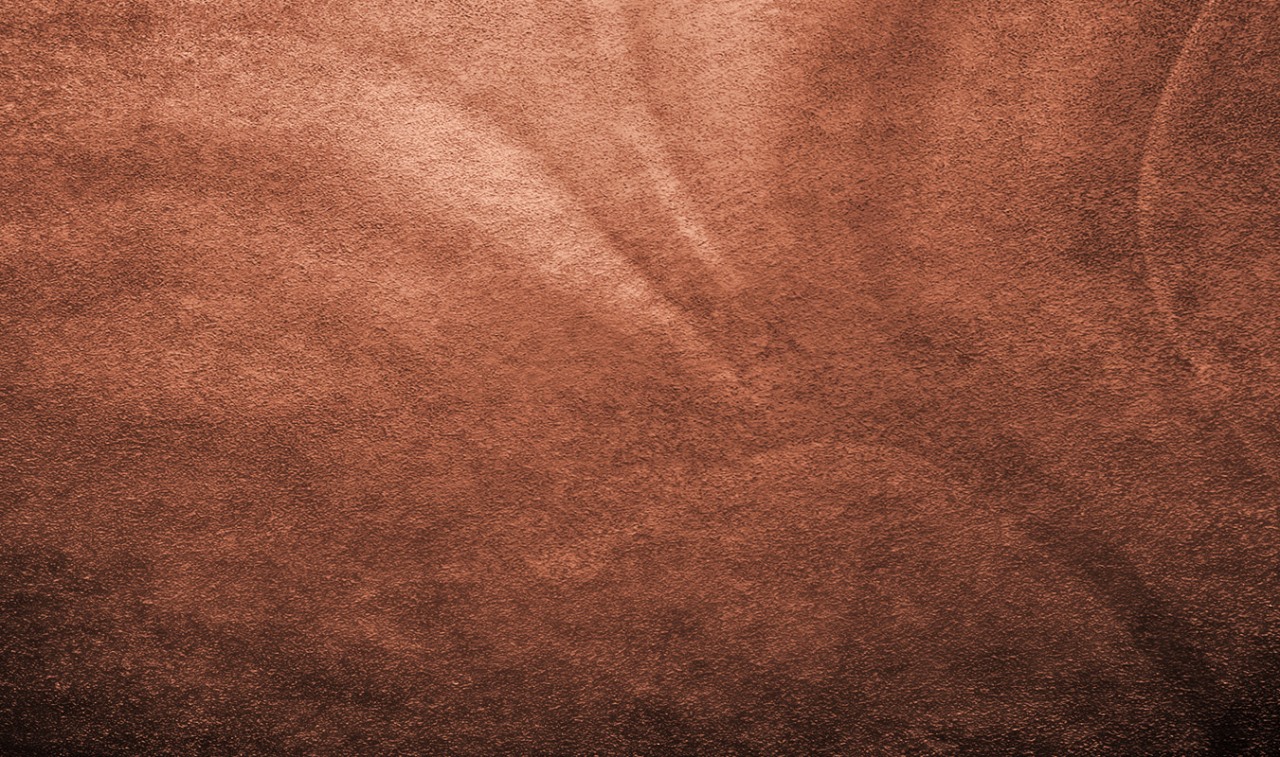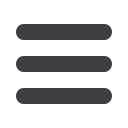

抒情敘事詩與濟慈之詩人本體的認同
267
緒推動力;沒有絲毫的懊悔,他讓鳥兒自行飛走了。詩人如此的舉
動,象徵性言,是詩人想「深埋」在第一階段時,過去的他和對鳥
兒世界未成熟的想法,並希望獲得新的自我。這些「悲傷的頌歌」
(第
75
行) 與「深埋」(第
77
行) 的用語可反映詩人想丟棄他的舊我。
此時,詩人不想與夜鶯「消逝」不見,但卻允許鳥兒自行「消逝」。
因此,在鳥兒消失前,它飛越過草原、小溪、山丘、河谷的林中空
地 (第
76
-
78
行)。湯姆斯‧馬法南 (
Thomas McFarland
) 以為這種
日常生活的熟悉景觀不具任何意義,所以最好將此刪去 (
1981
:
235
-
36
)。但是研究濟慈的大家傑克‧史令傑 (
Jack
Stillinger
) 卻認
定此些描述顯示了詩人較喜歡人間 (
1982
:
469
)。筆者以為如上的解
讀均合理:簡言之,濟慈本欲自鳥兒世界獲得願望滿足,以代償其
於塵世的匱乏;然,這終究只是幻夢一場,他仍得回到現實。在此
架構下,在第
79
-
80
行時,詩人有了一個新的思考向度;而它讓詩
人有了新的立場:詩人的心意未定且互相抵觸。
由上文推知,詩人有內心的衝突:在詩人本體上,濟慈與自己
辯論他該選擇那種觀點。他猶豫未決,而此種模擬兩可的心態令詩
人第三次改變立場。詩人質疑他的想像之旅是真,抑或是幻:「這
是一種幻像,或是一個醒時的夢?/飛逝的是音樂:──我是醒著
的或是睡著了?」(第
79
-
80
行)。如果詩人的想像之旅是真的,他
應該自此旅中學到智慧,且有包容與超脫的視野,就如布雷克
(
Blake
) 在《天真之歌》(
Songs
of
Innocence
) 與《經驗之歌》(
Songs
of
Experience
) 所假設的一樣?或是他仍與以前一樣,然後清描淡寫地
把那段暇想當作一個「醒時的夢」?因此,詩人加入了一種形而上
及互相對立的辯論。在下一行詩中,這種兩極化再度被強調:「我
是醒著的或是睡著了?」對詩人而言,他搖擺不定的態度並非是外
在感官對於夢/睡或是醒來的感覺,但卻是個攸關其存在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