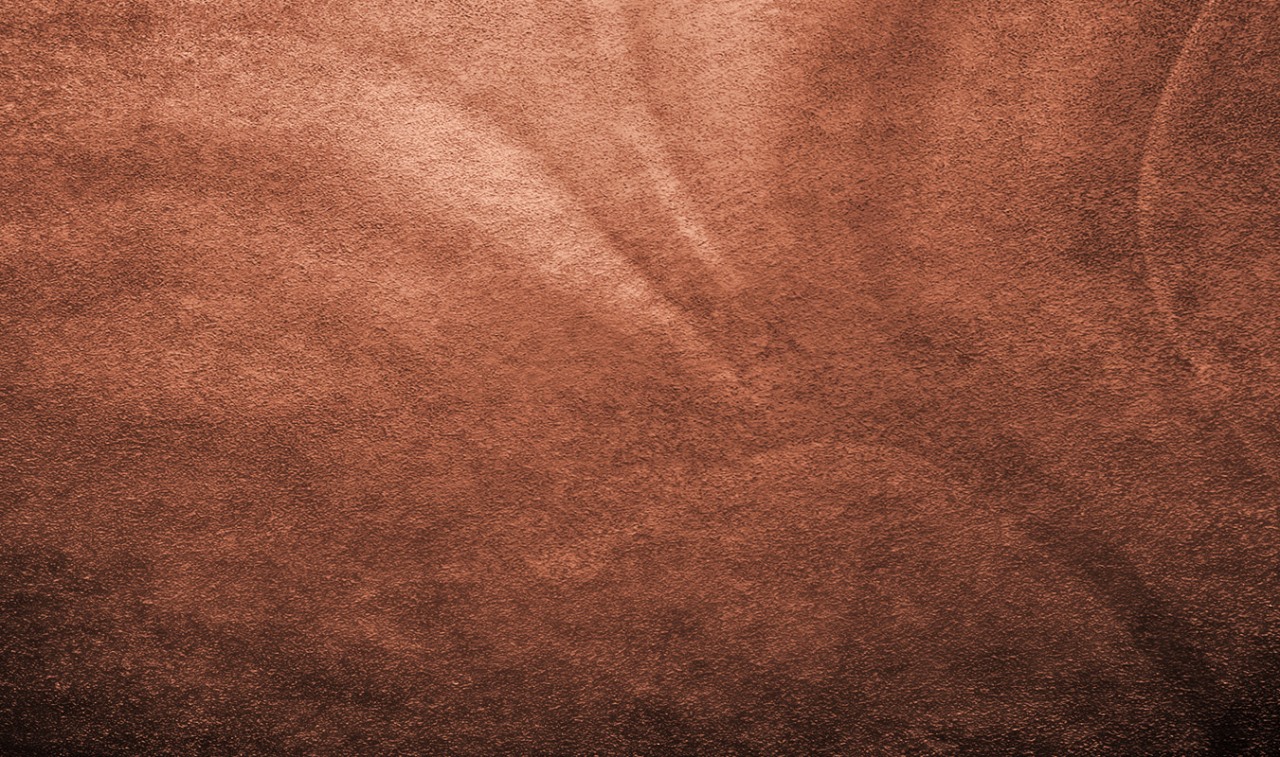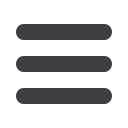

身體姿態與語言表達
145
系譜學區分,那麼這必須預設人類具有普遍的語言能力,且這種語
言能力在民族的語言發展過程中,又必須具有彼此差異但卻內在一
致的性格。這種在普遍中存在差異的現象,並不能單純從地理分離
的自然演進結果來解釋,而應看成是人類精神「需要造就豐富多樣
的智力形式」的「內在需要」(
1908
:
621
)。這是因為洪堡特主張語
言是一個整體,任何一個詞語之所以是一個詞語,都必須預設它是
在一個結構完整的語言中才是可被理解的。在這個意義下,任何語
言作為有機體,只能出於人類精神的創造,而不能單單透過機械自
然的解釋。他因而說:「語言必出於自身,而且無疑只能逐漸形成,
但是它的有機體並不是一種幽閉於心靈深底的無生命質料,而是作
為一種規律決定著思維力量的各種功能」(
Humboldt, 1905
:
15
)。
2
相對於
Bopp
等人的觀點,洪堡特認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語言
分類,是建立在豐富多樣的人類精神表現形式之上,而不是像植物
分類學那樣,只基於自然演進的過程。這使得當時對語言作為有機
體,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。像是把著作題獻給洪堡特的
K
.
F
.
Becker
(
1775
-
1849
) 在《語言的有機體》(
Der Organismus
der
Sprache
,
1827
) 中,即跟隨洪堡特主張,語言之所以是有機體,是因為它受
人類知性的邏輯範疇所影響。但相對的,在當時更有影響力的施萊
歇爾
(
A. Schleicher, 1821-1868
) 則除了在《語言學研究》
(
Linguistische
Untersuchungen
,
1850
) 與《印歐語比較語法綱要》
(
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
Sprachen
, 1861
-
1862
) 中,將原來在洪堡特的研究中,視為是精神
之不同表現形態的各種語言類型,理解成是從以漢語為代表的單音
節語,過渡到黏著語與以印歐語為代表的屈折語──這種由低等形
2
中譯參見洪堡特
(
2011: 23
)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