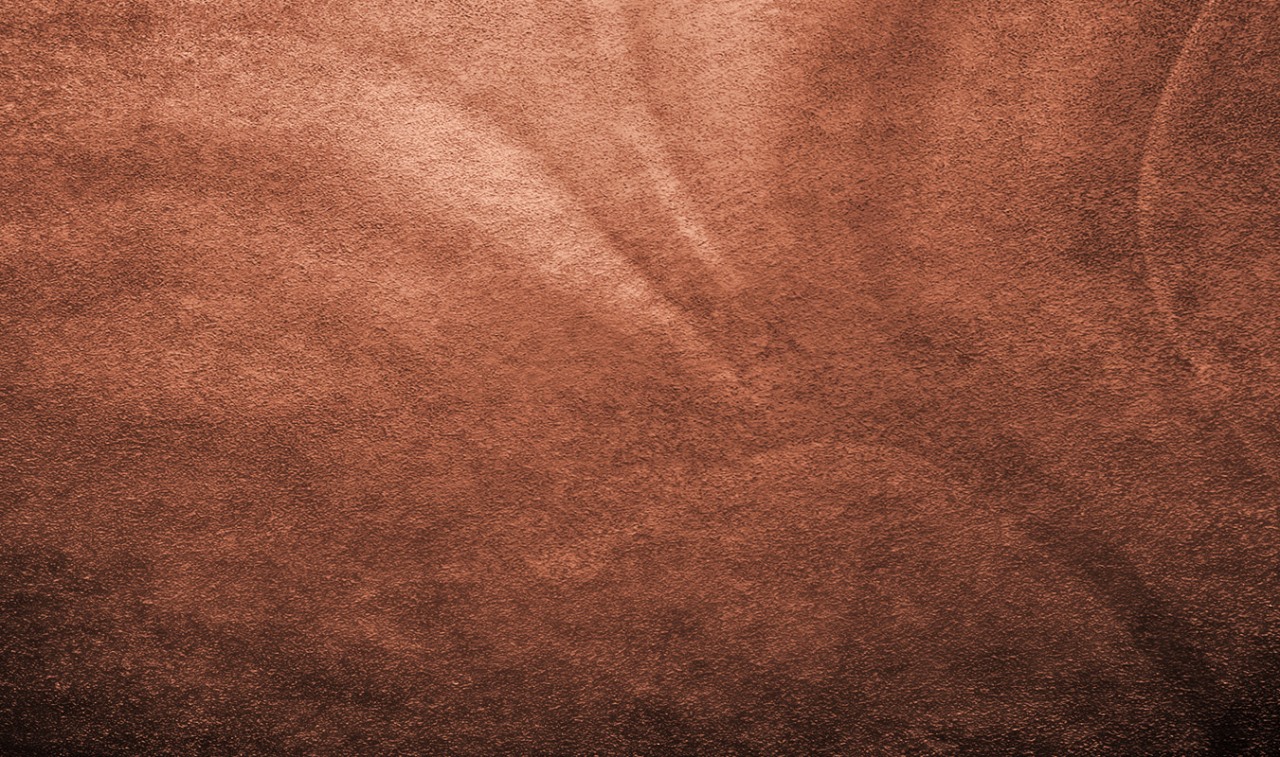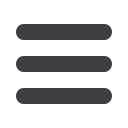

166
歐美研究
上留下痕跡,它因而成為一個人持續的情緒方向或主導他的熱情的
記號。吾人經由表情的運動所完成的內心表達,因而仍是科學可及
的研究對象。
14
馮特既反對將面相學單單應用於對人之性格的實用論斷,也不
贊同情緒表達的身體運動只是純粹的生物學現象。相對的,他在藝
術的展演中,找到面相學應用的正當領域。並宣稱面相學的研究可
以不只是基於外表的猜測,而是能對其運作的心理學原則進行科學
的研究。在面相學的藝術應用方面,馮特得益於
Johann
Jakob Engel
(
1741
-
1802
) 在《戲劇的理念》(
Ideen
zu
einer Mimik
,
1785
) 與
Emil
Harleß
(
1820
-
1862
) 在《雕塑解剖學教本》(
Lehrbuch
der
plastischen
Anatomie
,
1876
) 中的研究成果甚多。
Engel
是戲劇學家,戲劇必須
借助演員的表情與身體姿態來進行思想與情感的表達,
Engel
因而
嘗試從過去所有的創作中,抽象出特定的表達規則 (見圖
2
)。而
Harleß
則認為,若我們要雕塑出像拉奧孔 (
Laocoon
) 那種在快被蛇
絞死前的掙扎與痛苦的表情,就要對人的表情進行臉部肌肉等身體
表現的研究,以理解要如何透過嘴型與眼晴等臉部肌肉的表現,來
14
面相學對於理解人類內心的重要性,在馮特之前也早為哲學家所知。像康德在《實
用人類學》中,就想在
Porta
與
Lavater
的觀點之外,討論如何以面相學這門做為
「從一個人可見的面部形象,也就是從他內心的外部表現來做判斷的技藝」,來
說明個人的性格。黑格爾甚至在《精神現象學》中,把面相學放在他論主觀理性
之觀察理性的最高階段,認為這種「對自我意識與其直接現實的關係的觀察」,
是比觀察思維的邏輯或心理學規律更高的精神發展。不僅在哲學方面,在科學方
面人類情緒表達的重要性,也受達爾文的高度重視。達爾文在前揭書《人類與動
物的情緒表達》中,嘗試提出一種關於表達運動的生物學理論,他將此解釋成是
一種「根源性的行動殘留」。亦即,任何特定的情緒表達都是一早先具體的目的
性行為的弱化與殘留。例如憤怒的表達即是攻擊運動的弱化圖像,害怕則是防衛
的弱化。這是行為主義的研究根源,亦即想從行為的殘留來理解人類情緒等的心
理活動來源。